姐弟-丽红之声北京不眠夜
十多年前似乎应该尘封的一些细节因为时间的堆积而愈来愈重,小女孩牵着弟弟的手,在即将消逝而又不断延伸的途中,急急地走。
死亡是一种虚无,而虚无是多么大的力量,它无处不在。 十多年前似乎应该尘封的一些细节因为时间的堆积而愈来愈重,小女孩牵着弟弟的手,在即将消逝而又不断延伸的途中,急急地走。 让我们折回到过去,因为忘却总不能如愿来临。 有一个小男孩,他3岁的时候得了严重的肺炎,病愈之后就再也不会说话了。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几乎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会回过头来多看他一眼。他们说,这孩子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 小男孩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姐姐,他们一起长大。姐姐很爱这个不会说话的弟弟。只有她能从小男孩美丽的眼神里看明白他想说的话。 后来姐姐到了读书的年龄,她和别的孩子一起背着书包去上学了,但是小男孩不能去。他一大早起床,像一条小尾巴一样跟在姐姐的后面,静静地看着她匆匆忙忙地洗脸刷牙,然后背上书包小跑地出门去。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他小小的身影站在蓝天下,远处是人们行走说话和劳作的声音。春天的阳光爬上了麦秸堆,小鸟在歌唱,空气里有草叶和花朵混合的芳香——每一个这样美好的清晨都让人愉悦欢欣,谁会去注意一个不会说话的小男孩,注意他乌黑的眼眸里静静流淌的悲哀呢? 人的本性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呢?弱小者值得同情也许只是因为弱小者的卑微? 姐姐把他带到了学校,村办小学的老师们都喜欢这个仿佛从年画上走下来的男孩子。他们热情地教他画蜡笔画、写字,甚至允许他站在学校里唯一的那架钢琴前,把手指按在黑白分明的键上。可是孩子们却不喜欢他,他们不能容忍这个小哑巴竟能画出全班最好的画,不能容忍他的手指竟能碰触他们无法碰触到的琴键,不能容忍他竟如此受到老师的宠爱。有好事的孩子开始笑话那个姐姐:“你瞧你瞧!你的那个哑巴弟弟!他只会说啊啊啊!” 姐姐是个脾气暴躁又倔强的女孩儿,她和所有出言不逊的小同学们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她怒气冲天的样子反而使“来犯者”们乐此不疲。 弟弟用眼睛告诉姐姐,他不想再去学校了。 小男孩天天搬了一只小木凳坐在门前等姐姐回来。他看着檐上挂下的雨丝儿,听它们发出淅淅沥沥的轻脆的声音;门前的槐树落下洁白的花,鸽子走到他的脚下咕咕地朝他叫,阳光在他的头发上跳舞。他的手里握着一把蜡笔,他画老师,画钢琴,画扎着马尾辫的姐姐愤怒地向嘲笑他的人挥舞手臂的样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村里每一年的11月9日都有热闹的庙会,那一天恰好是小男孩的生日。上小学三年级的姐姐牵着弟弟的手在拥挤的人群里像两尾小鱼般游走穿行。走着走着,姐姐总是听到有尖锐的声音在叫:那个小哑巴!你们看那个漂亮的小哑巴! 庙会还没有结束,姐姐便急急地要带弟弟回去。她怕再碰到她的那些同学,她选择了走小路,路的两旁是村里的渔塘。那时的天气要比现在冷,也许那天的路面上有薄冰,可是这个自私的虚荣的姐姐只听她的同学的笑声:那个小哑巴!那个漂亮的小哑巴! 姐姐走得很快,尽管她从小男孩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委屈和不情愿。她拉着她的不会说话的弟弟的手,就像以前的无数次一样,那只手听话地放在她的掌心,没有一点点违逆。 姐姐,你讨厌我不会说话吗? 姐姐,你不再喜欢我了吗? 姐姐!你走得太快了! 姐姐!姐姐!姐姐! 那个村里有名的疯子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渔塘边徘徊,他一遍遍地绕着渔塘打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两个孩子落水的时候,疯子奋不顾身地跳入了水中,他动作的果断敏捷令不远处目睹了这一幕的一个妇女瞠目结舌。 两个孩子都被救了上来,可是姐姐在高烧两天后醒来却再也找不到她的弟弟——小男孩死了。他美丽的大眼睛不会再睁开,他不动也不笑,他的小手像冰块一样冷。那个铸成大错的姐姐并不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她以为她的弟弟就像她生命的一部分一样是不会消失的。可是一只小小的木盒子里装着弟弟的骨灰,许多天过去了,她的弟弟没有像以往的无数次一样蹦蹦跳跳地迎到她的跟前来。她再也握不到那只乖驯地放在她掌心的小手。她再也看不见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开始恐慌起来。 姐姐不去上学,她也不说话。她听说那个救他们上来的疯子在家躺了一天后居然不疯了。有人说是被冻醒的,但也有人说是弟弟的魂附到了他的身上。为了后一种荒谬无稽的说法她整天跟着那个“疯子”,赶也赶不走,于是弟弟的妈妈只好写信给姐姐在市区工作的妈妈,让她把姐姐带了回去。 那个姐姐就是我,那个弟弟是我的表弟。 我休了一年的学,在那一年里,我总是跟电线杆、树桩子、小水桶甚至一堵墙说话。像一个痴呆儿童,而实际上也许就是这样。对这一年的记忆我很模糊,唯一清楚的是那一双眼睛,留在记忆的底线,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都不曾离去。我的快乐至此再不能彻底而纯粹,我变得好脾气,听话又谦让。村里人偶尔进城来看我,都惊异于我的变化。 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能原谅你,而唯独不能原谅你的正是你自己。也许只有当事情发生后,你才会体会到那种不能回头的绝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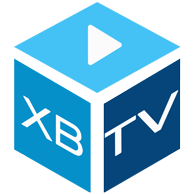 西贝视听
西贝视听